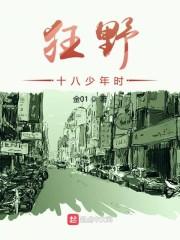还 钱(第1页)
里明
一
陈初五赶到春晓饭店时已经是晌午了。饭店门口停了不少摩托车,农村人停车很不讲究,横七竖八的,就像是停在自家的院子里。陈初五开着他那辆蓝色的三马子,在饭店门口转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车位,最后只得开到饭店后面一片背人的空地上。
他拔下车钥匙,车辆瞬间停止了轰鸣和震颤。他下意识地瞅了瞅满满的一车砖,心中嘀咕一下,似乎在担心什么。正午的太阳照得他有些睁不开眼,他脑子里浮现出一句话: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人偷砖呢。他一边往前走,心里一边嘀咕:大中午的,不就是吃顿饭吗,砖肯定不会丢的。直到走进饭店,他仍旧在担心他那一车砖,即使周围是杂乱的喧闹声。直到他坐到好朋友王文法的对面,他心中还是顾虑重重的:那一车砖绝对不会有事,大白天怎么会丢呢。陈初五是应王文法之邀,来一起吃饭的,两个人干得都是一样的活计,拉砖。
桌上的三盘菜都是硬菜,一个热菜是小鸡炖蘑菇,两个凉菜分别是腱子肉和拌牛肉,有好菜必有好酒,一瓶当地产的青花小雕。美味窜进了陈初五的鼻孔里,唾液在嘴中滋生,肠胃里好像伸出一只小手,要去抓一片牛肉。他好酒,在农村很少有男人不喝酒的,不喝酒都上不了主席,只有女人才不喝酒。
他拿起酒瓶,边倒酒边问:“哥,嫂子啥时候生?”
“就这两天,就在县医院。”王文法说。他同样馋酒,几乎是逢酒必喝,有时候喝多了就爱吹牛胡扯,人送外号“文法大仙”。在这一点上,陈初五就和他不同,陈初五喝多了,就爱闷头睡觉,他也有个很贴切的外号,陈葫芦。
他俩是从小光屁溜长大的发小,王文法比陈初五大一岁。他俩从小关系就铁,就好像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王文法去偷人家树上的柿子,陈初五就是那个把风的。陈初五掏裆学骑28自行车的时候,王文法就紧跟在后面,紧握住车后座,稳住车身,生怕他摔倒,尽管他也才是个八九岁的孩子。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畅谈尽欢,王文法话多,他就说起来没完,陈初五话少,他就竖起耳朵听。陈初五下午还得给人家送砖,这根弦始终绷在心里。但看到王文法说得起劲,他好几次想打断他,都不忍张口。他怎么能张口呢,即使迁就自己,也不能扫了王文法的兴。这顿饭已经吃了一个多小时,此时,王文法酒饮微醺,脸泛红晕,啃着鸡腿,半截骨头露在外面,半截骨头塞在嘴里,顶在左腮上,鼓出一个小包。陈初五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顿饭上了,实在是太晚了,不能再耽搁了。他把筷子放到桌子上,盯着王文法的脸,连吸了三口气,好像是在给自己壮胆,他捏了一下鼻子尖,又抓了一把下巴颏,支吾地说:“哥,吃得挺好,要不……”还没等他说完,王文法抢先说:“初五,你下午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要有事,你先走,没事,你不用管我。”陈初五本应该借坡下驴,抬起屁股就走,哪知他心思稍有迟疑,竟顺口说:“没事,没什么事,我不着急。”说话时,嘴咧开一道缝,龇牙笑了两声,很快,这道缝就闭上了,后槽牙狠狠地咬在一起。
吃完饭时,两个人走出饭店,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陈初五老远就看到自己的车有些不对劲,砖明显是少了,露在车顶上的那两层砖已经不翼而飞,果然有人偷砖。他懊恼地一跺脚,疾跑几步,嚷道:“真他娘的有人偷砖。”他围着车转了三圈,过了一下数,大概丢了两百块。他心里不住地骂娘,这可咋整,人家下午等着要砖呢,再赶回砖厂重新拉,已经来不及了。这时,王文法把车开了过来,他说:“初五,你这个车停的不是地方,太背了,谁也看不见。”陈初五叹息一声,两手一摊,无奈地蹲在地上,捡起一小块碎砖头,紧握在手中。
“初五,没啥的,不就丢了几块砖吗,拿我车里的砖,先给人送去要紧。”王文法说。这倒是个好办法,也只能这样了,两个人急忙开始搬砖,一块块红砖从王文法的手中递到陈初五的手里,重新摞了起来,填补了丢失的缺口。陈初五还想说句感谢的话,话刚到嘴边,还没说出口,王文法拍了拍陈初五的肩说:“快走吧,路上慢点开。”
这一天,陈初五送完砖,急急火火往家赶,直到夜里11点才到家。老婆桂枝已经睡了,门口的房檐上给他留着一盏灯。陈初五拍了拍满身的浮灰,在缸里舀了一瓢水,仰着脖子大口地喝了起来,又就着脸盆里不多的水,洗了一把脸。借着昏黄的灯光,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沓钞票,一张张地数起来,一百、二百、三百……最后连零钱都算上,总共是443.5元,这是他今天的卖砖所得,刨去成本,共赚了78块钱。
第二天,陈初五没有拉砖的活,正好腾出功夫来拾掇家里。陈家的老宅还是30多年前他爷爷盖的,看上去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到处显现着它的残破。房顶还是那种黑色的瓦片,上面恣意地长着杂草,长短不一的秸秆从房檐下露出来,外墙面粘贴的一些几何图形斑驳不堪,两扇木制的对开大门已无法关严,露出一道黑乎乎的缝。
陈初五他家在草碾村,位于燕山东麓,他家祖祖辈辈就住在这个小山村。陈初五他爹死得早,在他五岁的时候得肺病死了。后来娘扔下他改嫁了,他就跟着爷爷奶奶过。再后来,爷爷奶奶相继过世,他便无依无靠了。直到经人介绍他认识了桂枝,到后来两个人结婚,才算有了自己的家。他总说自己从小就没有家,没有爹,没有娘,不知道爹娘长啥样。他恨他爹,更恨他娘,好像这种恨,从小就伴着他成长,在心里生根发芽了。他还作了一首诗形容他小时候:生于腊月五,从小命就苦,没爹又没娘,米汤加糊糊,日子天天挨,有苦无人诉,倘若有来生,愿用命来赎。
房子的问题先搁一边,陈初五站在西北角的院墙旁,正在修补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院墙有一人多高,陈初五踩在梯子上,半截身子露出墙外。地上摆放着一盆水泥和一摞砖,他老婆桂枝在一旁给他打下手。农村的女人干活都利索,一年四季没少干农活,全靠两只手和一身的力气。桂枝蹲在地上,右手拿起一块砖,左手麻利地抹上一层水泥,随手向上一扔,陈初五只需轻轻一接,那块砖就像磁铁一样吸在他手上。陈初五在上面一块一块地砌,桂枝在下面一块一块地扔,两口子真是砌砖的熟练工。缺口越来越小,院墙马上就要砌好了,陈初五低头瞅着下面说:“再来最后一块。”此时,桂枝抹好最后一块砖,一只手扶墙,缓缓站起身来,踩在一块砖头上,踮起脚尖,一只手将砖高高举起。在陈初五正要接,还没有接的当口,他猛地发现墙外的村道上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他认识,是王文法的二姑。远远望过去,二姑头也没怎么抬,一路小跑脚步匆匆,这肯定是有啥急事。
“二姑,咋了,这是有啥急事。”陈初五扯着嗓子喊道。二姑脚底下走的急,并没有听到有人叫她。于是,陈初五又高声喊道:“二姑,二姑。”这回二姑听见了,她停住脚步,抬起头,向四周张望,在一片繁茂的草木后面,她看见了从院墙里探出脑袋的陈初五。二姑是看着陈初五长大的,关系一直很好,她走到近前,仰着头,不无焦虑地说:“出事了,出事了,你嫂子生孩子大出血,正在医院抢救呢。”陈初五很是吃惊,他甚至都有些不相信,怎么可能,昨天还好好的呢,他急切地问:“那现在怎么样了?”二姑说:“正在抢救、正在抢救,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借钱去,摊上这样的事,家里有多少钱也不够花啊。”
最后这一块砖,陈初五到底是没有接在手里,院墙上还是留了一小块缺口。陈初五从梯子上一跃而下,一步没站稳,打了个趔趄。他很焦急,就好像这件事是发生在他老婆身上一样,他对桂枝说:“你也都听到了,王文法的老婆生孩子大出血,我不能袖手旁观,家里还有多少钱,我给他拿过去。”听完这话,桂枝板起脸来,将手中的砖头往地下一扔,说:“陈初五,你是傻你是呆,你有多少钱可以借,咱家的钱是留着盖房子的,家里的钱你一分都别想动。”陈初五没有理这个茬,他执拗地说:“你懂啥,王文法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个钱我非要拿。”说罢,他急冲冲地就往屋里跑,桂枝也不是省油的灯,跟在后面大喊:“不能借就是不能借。”女人到底是没有男人劲大,尽管桂枝在一旁不停地阻挠,又拉又拽,还是眼睁睁地看着陈初五从柜子里拿走了2万块钱。这2万块钱好像是桂枝的心头肉,被陈初五一勺子刮走了。她跪在天井当院,抓起一个苞米头,狠劲地向大门口扔去,嘴里不住地念叨:“陈初五,有你后悔的那一天。”
陈初五开着三马子火急火燎地往医院赶,车后斗的几块砖头颠簸的上下翻飞。一个电话打过去,先是安慰几句,紧接着就说2万块钱马上送到。他要提前让王文法知道他的好意,他要让王文法安心,只有王文法安心了,他心里才能滋生出如绚烂烟花般的满足感。在医院的走廊里,他把2万块钱交到王文法的手中,嘴里不忘说上一句:“哥,这是2万块钱,我一听到这信儿,一刻也没敢耽误,赶紧就把钱给你送过来。”此时的王文法心力交瘁,他接过钱,只是简短地回了句:“初五,谢谢。”一众王家的老老少少焦灼地守在产科门口,陈初五不是亲属,自觉地站在走廊的最外头。他左肩倚靠着墙,踮起右脚脚尖,伸长脖子,半张着嘴,抬眼看到王文法拿着一摞钱,其中也包括他那2万块钱,在和医生交谈着什么。
上午的阳光温煦而光亮,充足的光线照进走廊内,不偏不倚,有那么一道正好照在陈初五的脸上,让他的脸看上去很明亮,很夺目。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来送钱的,只要把钱送出去,他就算占领了心灵上的高地。一直以来,他总觉得自己亏欠王文法的,今天不仅彻底地还了人情,而且还打了一个翻身仗,他真是感觉心里舒坦,整个人如沐春风一般。但他不能显露出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悲戚的表情,他不能显现出他的愉悦,他一样是面露苦色,时不时还搓两下手,跺两下脚,或者发出一声急促的叹息。
王文法写好了一张张的借条,递给众人,借条上各家各户金额不等。其中二姑的是五千,二姨的也是五千,大舅家是一万,小姑家是八千,陈初五的最多,是两万。事情办得挺敞亮,敞亮的如同正午12点的太阳,照进陈初五的心里,熠熠生辉。陈初五接过借条,一张不大的小纸条,上面有王文法的亲笔签名,字写的比较草,看上去像“玩去”两个字。
陈初五回去了,两万元现金换成了一张借条。他整个人轻飘飘的,轻踩着油门,轻哼着小调,就像踩在一团棉花上。在他看来,其实借条都是可以不要的,是王文法硬塞到他手里的。他把借条拿给桂枝看,他仍然想得到老婆的认可。此时的桂枝已经无话可说,还能说什么,这个败家的男人已经把钱借出去了,她只得无奈地说:“借钱可以,谁都会有个难处,可咱也要量力而行,总共就2万块钱,是留着以后盖房子用的,你一下都给借出去,你想过没想过他什么时候还。”说实在的,陈初五还真没有想过还钱的问题,当时只是一股脑的要把这个好人做到底,要把这个多少年欠下的人情窟窿给他填上,还真没有想得那么长远。他只得勉强地说:“还钱,他肯定会还的,他会还的,这不是还有他的借条吗。”
半个月之后,王文法打来电话,说刚刚出院,母女平安,他再三表示感激之情,说改日一定登门拜谢。陈初五像个救命恩人一样,说了很多客套话,他说无非是借了一点钱吗,也没有帮什么大忙,只要人没事就好,临了还特意说,还钱的事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先还别人的钱,他的钱可以最后再还。
二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陈初五和王文法,各拉各的砖,各干各的事,各挣各的钱。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陈初五的脑袋里多了一根弦,这根弦上挂着2万块钱,总在那里不住地摇晃,晃的陈初五心里发慌。
可陈初五万万没想到,这根弦一晃就是五年。在最初的一年,陈初五没有指望能拿回那2万块钱,毕竟王文法家也不富裕,孩子刚出生,老婆产后大出血,命差点没丢了,这个家没有一年半载根本就缓不过来。相反地,隔三差五的,他还经常拎着糕点、水果上门看望。他特别喜欢王文法的小女儿丹丹,总是把她抱在怀里,又是逗又是亲,好像是自己的女儿一样。等到第二年,陈初五还是没有等来还钱的希望,王文法大部分钱都用在给老婆买药了,哪还有钱来还债。等到第三年,王文法的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老婆的病也恢复的差不多了,他终于可以还钱了,可是仍然没有轮到陈初五,王文法先还的是亲戚们的钱。
陈初五此时已经想不起当年借钱时的爽快了,好像那是很久的事,都有些记不清了。他时常会翻出那张有些泛黄的借条,上面的字迹都有些模糊了,但这的的确确是一张借条,上面还有王文法的签名呢。在这几年,还钱的事经常溜进陈初五的心里,搞得他心烦意乱,有时他会对着天空发呆,有时他会看着河水发愣,甚至有一次他直接把车开进了水沟里。但他从没有跟王文法提钱的事,他张不开这个口,他要等到王文法主动还钱的那一天。到了第四年,王文法干起活来更加卖力,经常没日没夜的拉砖,其实他心里也很着急,欠债的日子并不好受,好像有人在后面拿小皮鞭抽他,而这个人就是陈初五。陈初五越是不说,他心里越过意不去。一切的迹象表明,用不了多久,王文法就能把钱还上了。可是偏偏要发生一些事,让他无法还上这个钱。
一天晚上,拉了一天砖的王文法开着三马子匆匆往家赶,被对面的车灯晃的睁不开眼,没注意到旁边骑行的一辆自行车,稍不留神,没有避开。结果把那个骑车的人撞得在地上打了三个滚。陈初五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看看那个趴在地上痛苦呻吟的老人,他气恼地抓住王文法的肩头说:“哥,你这是咋开的车嘛,你看把人撞得。”他真想给王文法两个耳光,并告诉他,你他娘的把人撞死都跟我没有关系,但你得还我那2万块钱。可是他没有说,他不想说,更不敢说,他不能跟王文法提钱。虽然他知道,看眼下这个情形,自己的那2万块钱又要泡汤了。陈初五和王文法拉着那个老人去了县医院,做了检查,老人左小腿骨骨折,还好并不是太重。尽管如此,包括手术费、住院费和各种赔偿也花了将2万块钱。王文法特意把一沓费用清单递到陈初五面前,懊恼地说:“刚攒点钱,这一下子又光了。”那意思是说,陈初五,不是哥不还你那2万块钱,实在是没钱还。陈初五真是欲哭无泪,好像有人在故意捉弄自己,刚刚让你看到点希望的火光,一股风吹来又灭了。心里的火光灭了,嘴上的热忱不能灭,他反而安慰王文法说:“哥,没关系,不就2万块钱吗,破财免灾。”
时间已经来到第五个年头,当年的那笔借款,好像存放在一个尘封已久的木匣里,再也无法打开。农历大年初二的早晨,陈初五在后院劈柴,长斧子被他高高举起,重重落下,每劈一下,圆木一分为二,他嘴里立时喊出“还钱”二字,声音犹如撕裂一般,带着凄厉的颤音。桂枝在一张白纸上,抹好了浆糊,要修补一块破玻璃,这是昨晚刮大风刮得,这是这个冬天她糊的第三块窗户。这所老房子犹如一件破旧的大衣,需要经常来缝缝补补。这五年来,因为借钱的事,她心里是憋着气的,这股气犹如上下跳跃的火焰,不时的在她心间灼烧。她站在窗户底下,吃力地仰着脖子,小心翼翼地将白纸对准玻璃裂口,她的手沿着破玻璃边缘轻轻按压。很不巧,在一瞬轻微的疼痛之后,她的右手指被锋利的玻璃划破,鲜血瞬间流淌出来,沾染在白纸上。她骂了句:“娘的。”将手指吸吮在口中,她尝到了鲜血的味道。她吐出一口红色的唾液,两只眼睛也好像变红了,她冲着后院大喊:“陈初五,你个孬种,你不去,我去。”说着,她狠劲勒了一把棉裤带,使劲提了一下布棉鞋,甩开胳臂,发疯似的朝院外跑去。陈初五听见了桂枝的喊叫,起初他没往心里去,直到把面前的劈柴砍完。他猛然想起老婆刚才说得话,他慌忙甩掉斧头,下意识地说了句:不好。他在屋里转了一圈,见没有人,又冲出院外,站在门口,顺着村道,望到了桂枝愈发远去的身影。陈初五气炸了,就像一滴水溅到了油锅里,他一边跺脚一边踹墙,气恼地说:“傻娘们,你这是要干啥,大过年的,你这是给我惹事,给我添堵。”
也就是片刻的功夫,陈初五开着三马子,风一般的向桂枝追去。到底是两条腿走得没有车轮子转得快,在快要到王文法家的时候,陈初五把车横在了桂枝的面前。他一把拽住桂枝的胳膊,说:“能不能消停,大过年的,你这是要干啥。”桂枝并没有顺从,她拼命地想挣脱开,“陈初五,你甭管,我就是想要回那2万块钱,五年了,整整五年了,你不要,我来要。”陈初五也是窝了一肚子的火,谁曾想这事能到今天的地步,但他仍旧执拗地拦住桂枝,他说:“老爷们的事,你就别掺和了,我会要的,他又没说不还。”桂枝把心一横,认定了死理,她说:“不行,你说话跟放屁一样,鬼才信。”
两个人的争吵声惊动了四邻,王文法第一个从家里走出来,他也很好奇,他似乎听到了有人叫他的名字。他站在不远处,眼前居然是陈初五两口子吵架,这大过年的,多晦气,多不吉利。他快步走上前说:“初五,为啥嘛,吵啥嘛。”这事闹的,真是有些冤家路窄,桂枝瞪了王文法一眼,她甚至想一直瞪下去,但也就是一刹,又气呼呼地把头扭向一旁。她真想上去拧住王文法的脸,把这件事挑明了,但她没有这样做,她或许只是想闹一闹,只是想发泄心中的不满,她是想给自己男人足够的面子。
陈初五的脸色阴一阵、晴一阵,很不自然,他先是对着王文法干笑几声,以体现出最基本的客套,又愤愤地瞅着桂枝,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他的心思不停翻滚,犹如热锅里的油条,他想:老婆啊老婆,你要闹就闹到底,你倒是接着闹啊,你就跟王文法说,让他还钱,赶紧还钱,越快越好,你怎么不说了呢,你的本事呢,你要是不说,我怎么张得开口啊。桂枝到底是没有开口,她怎么能张口呢,她如果张口了,那陈初五的面子往哪搁,钱既然是男人借出去的,也要男人要回来才行。她在掉了两滴眼泪后,默默地选择退出,临走前还嘱咐一句:“初五,少喝点酒。”
王文法家的院子远比陈初五家阔绰,高高的门庭十分大气,上面挂着一块横匾,镌刻着“小康之家”四个字。四间敞亮的红砖瓦房,看上去干净整洁,地面是一水的瓷砖,上面是纵横交错的花纹。房顶上甚至还装了一台太阳能热水器,陈初五抬起头瞥了瞥那台热水器,随口问:“那东西多少钱?回来我也买一台。”王文法说:“两千多吧,年前买的,洗澡特别好使,龙头一拧,就有热水。”陈初五的嘴角不禁抽动一下,他是真没往心里去,他也不想太较真,可是他的心仿佛被锋利的麦芒扎了一下,顿时感到一阵的疼痛。
一进入屋里,王文法的小女儿丹丹就迎了过来。陈初五把丹丹抱在怀里,丹丹摸着陈初五的脸,用稚嫩的语气说:“五叔,新年好。”陈初五脸上乐开了花,对着丹丹的脸蛋,左亲一下,右亲一下,说:“丹丹好,丹丹新年好,丹丹越长越漂亮了,这小脸蛋多讨人疼啊。”他举起丹丹在空中转了三个圈,把丹丹逗得笑起来没完。陈初五把丹丹放下来,在兜里摸了摸,掏出一百块钱来,递给丹丹,“来,拿着,压岁钱,压岁钱。”丹丹一看到钱挺羞涩的,小手握在一起就是不往外伸。陈初五说:“丹丹,你还不好意思哩。”王文法站在一旁,笑着说:“丹丹,拿着吧。”这时,丹丹才羞怯地伸出一只小手,接过钱,然后举着钱,一边晃一边向外屋跑去。
王文法的老婆忙前忙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这女人看陈初五就像救命恩人一样,又是递烟,又是倒茶,给他准备花生、瓜子,生怕怠慢了他。陈初五说:“嫂子,你不用这么客气,忙你的去吧。”他嫂子说:“那不行,你是俺们家的贵客,跟别人都不一样,俺们一家都忘不了你的恩情,对吧他爹。”王文法接过话茬说:“那可不,大恩不言谢,都记在心里哩。”陈初五嘴里嗑着瓜子,卡嘣一声,瓜子壳一分为二,他把瓜子皮吐在地上。他心里想:说一千道一万,扯这些都没用,要是真念着我的好,就赶紧还钱。但想归想,他不会吐露他的真实想法,他说:“嫂子,小时候家里没饭吃,我总来哥家蹭饭,大妈二话不说,让我跟文法坐一块吃,还给我夹鱼夹肉,我也不会忘了你们对我的恩情啊。”王文法呵呵一笑,说:“初五,你这个兄弟哥没有白交。”陈初五点点头说:“是啊,多少年的情分,老铁了。”
王文法从柜子里拿出两瓶洋河经典,说过年一直没舍得喝,就是为了等兄弟来一起喝。陈初五看着如美人纤腰般的蓝色酒瓶,啥也甭想了,大过年的,啥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谈钱多伤感情,钱就是一堆驴粪蛋儿,你真用它施肥,它还不如一坨大粪。他握住酒瓶的细腰,说:“哥,今天咱哥俩一定要喝个痛快。”两个人你一口,我一杯,觥筹交错。席间,陈初五问王文法,嫂子身体恢复的咋样了。王文法说,没事了,都能下地干农活了,我不让她去,她偏要去,拦不住,这不,年后还打算把后山的一块荒地开出来,要种棒子。陈初五一边喝酒,一边点头,心里想:既然嫂子身体都好了,就没啥负担了,那就赶紧还钱吧,还拖到啥时候。王文法举起酒杯问,你两口子大过年的为啥吵架,陈初五支吾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他要绕开还钱的事,他只得瞎编。他的眼神游移不定,酒杯举起又放下,在低着头沉吟片刻后,他说:“桂枝非要回娘家,我不让她回去,她就跟我闹。”王文法浅笑一声,说:“初五,我看这事就是你的不对,桂枝要回娘家,你就让她回去,你不仅不能拦着,你还要跟她一块回去,不就是待两天嘛,过年了嘛,都想见见亲人。”陈初五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点几下头,假意附和着:“不理她了。”随即举起酒杯,将杯中剩下的酒一饮而尽。
这顿酒喝得怎么就不是滋味呢,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当陈初五从屋里出来时,感到了阵阵的寒意。他瑟缩地裹紧身上的棉袄,望了望灰蒙蒙的天,一排排参天的杨树,笔直的枝丫上挂着些许枯叶,一群黑色的老鸹在头顶盘旋,发出嘶哑的叫声。忽地,在一股强烈的北风吹过后,他的双眼迷离了,他的内心竟感到一阵的凄凉。陈初五离开王家时,他那辆三马子很不争气,接连打火愣是没有打着。王文法说要不你开我的车回去,陈初五说没事,都是天太冷闹得。他拼命地拧车钥匙,一下不行两下,两下不行三下。在王家老老少少的注视下,约莫过了5分钟,他的车终于打着了。三马子发出轰轰的吼叫声,排气管喷出一股股浓烈的黑烟,好像放了一个巨大的烟雾弹。
陈初五骑在路上,冷风嗖嗖地吹来,灌进棉袄里,钻进袄袖里,冻的他瑟瑟发抖,不过身体一哆嗦似乎头脑就清醒了。2万块钱好像变成了紧箍咒,缠绕在他头顶上。回到家时,桂枝瞅着陈初五的窝囊样,又是一阵奚落,说不是叫你去王家喝酒的,是让你去要钱的。陈初五大声喝道:“要钱要钱,当初要不是借给他钱,哪来的这些鬼事。”陈初五醉醺醺的,蜷缩在床头,昏昏睡去,嘴里陡然蹦出一句话:“王文法,我和你没完,我要让你倒霉,倒大霉,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我的大佬妻子 雪豹:靠着抢劫打造最强精锐团 明末求生记 首届掌阅文学大赛中篇入围作品集:科幻篇 空间医女之穿梭古今做代购 首届掌阅文学大赛短篇入围作品集:悬疑篇 村长的后院 首届掌阅文学大赛短篇入围作品集:情感篇 娇软小乖乖,被抵门板亲哭 宝可梦之龙柱力 大叔宠娇妻 把死对头宠哭了,他怎么敢的! 我只破案,抓人有警花老婆 快穿系统:攻略狼性boss 天道轮回经 首届掌阅文学大赛中篇入围作品集:情感篇 首届掌阅文学大赛短篇入围作品集:文学篇 仙魔乱舞之辰狂寰宇 系统之诸天缔造 高武:SSS级治愈天赋成就最强
点道为止
功夫究竟是什么花架子还是杀人技三千年冷兵器战争和无数民间私斗酝酿出来的把式,究竟是不是骗局国术流开创者,功夫小说第一人梦入神机,在本书中为您揭秘。止戈为武,点到为止。你若无敌,将会如何...
田园食香
杜玉娘重生归来,发现自己回到了十二岁,悲惨的生活还没有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她想重新活一回,却发现,即便自己不再爱慕虚荣,渣男却依旧阴魂不散。难道她就摆脱不掉命运的轨迹了吗她收起了无知和虚荣心,要...
狂野十八少年时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当一个人的前一世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再次重生后是像上一世一样继续浑浑噩噩的过一生,还是走出一条不同于上一世的路在这世界留下自己生命的迹象...
小仙女有个红包群
诶,天上飘过来的那片云,长得好像一个二维码扫一扫叮您已加入群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天下太平一家亲要我做任务没问题,毕竟是收了红包的人。不过最后突然修成了仙,抱歉抱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斗罗之雷神传说
关于斗罗之雷神传说斗罗一续写宁枫,拥有着前所未有三生武魂第一武魂,雷灵可随着魂力等级提升而不断进化的超级进化本体武魂第二武魂也是继承了神之血脉的神器雷神之锤,站在了器武魂顶端的绝对霸主第...
官运红途
吴一楠无意间看到老婆在自家楼下跟市委秘书激情拥吻,继而得知自己的副科长职位是市委秘书帮的忙,愤而跟老婆离婚,随之被撤职换岗,人生处于低谷之中。现场会上,吴一楠对刘依然产生好感,对她勇敢反抗和揭露领导...